[古诗翻译]耍孩儿·庄家不识勾栏-作者杜仁杰
元 杜仁杰
风调雨顺民安乐,都不似俺庄家快活。桑蚕五谷十分收,官司无甚差科。当村许下还心愿,来到城中买些纸火。正打街头过,见吊个花碌碌纸榜,不似那答儿闹穰穰人多[三]。
[六煞]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,高声的叫“请请”,道“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”。说道“前截儿院本调风月,背后么末敷演刘耍和”。高声叫:“赶散易得,难得的妆合[四]”。
[五煞]要了二百钱放过听咱,入得门上个木坡,见层层叠叠团囗栾 坐。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,往下觑却是人旋窝。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,又不是迎神赛社,不住的擂鼓筛锣[五]。
[四煞]一个女孩儿转了几遭,不多时引出一伙。中间里一个央人货,裹着枚皂头巾顶门上插一管笔,满脸石灰更着些黑道儿抹。知他待是如何过?浑身上下,则穿领花布直裰[六]。
[三煞]念了会诗共词,说了会赋与歌,无差错。唇天口地无高下,巧语花言记许多。临绝末,道了低头撮脚,爨罢将么拨[七]。
[二煞]一个妆做张太公,他改做小二哥,行行行说向城中过。见个年少的妇女向帘儿下立,那老子用意铺谋待取做老婆。教小二哥相说合,但要的豆谷米麦,问甚布绢纱罗[八]。
[一煞]教太公往前挪不敢往后挪,抬左脚不敢抬右脚,翻来覆去由他一个。太公心下实焦燥,把一个皮棒槌则一下打做两半个。我则道脑袋天灵破,则道兴词告状,刬地大笑呵呵[九]。
[尾]则被一胞尿爆的我没奈何。刚捱刚忍更待看些儿个,枉被这驴颓笑杀我[十]。
注释
[一]耍孩儿:般涉调的一个曲调,也在正宫、中吕、双调的套数里运用,但没有单独作小令用的。这套曲借一个庄稼汉的口吻,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元代勾栏的情况。是研究元杂剧演出的重要资料。篇中虽然写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无知。但并没有丑化讥讽之意,却近于善意嘲弄。曲文描摹人物场景,历历如画,又纯用口语,生动活泼,颇近民间说唱风格。
[二]庄家:犹言庄家汉,即农民。勾栏。即构阑,宋元时演出戏剧杂要的场所,因其以栅栏勾连围绕,所以叫勾栏。
[三]耍孩儿全曲:这曲写庄家丰收,差科有限,以为神功保佑,进城买香烛纸马(纸火)还愿,偶然发现街头挂着的演出广告(花花碌碌纸榜),许多人围在那里看。差科,差役,租税。那答儿,那里。
[四]六煞全曲:这曲写庄家看到勾栏门口一个高声招徕观众的人,从他口里知道这次演出的两个剧目是院本《调风月》和么末《刘耍和》院本是由付末和付净两个角色主演的滑稽戏,内容比较简单。《调风月》是当时经常演出的院本。么末,即杂剧。刘耍和是金元间著名的演员,在金朝教坊里担任过色长(领班之类),见《辍耕录》及《录鬼簿》。他的故事后来被编为杂剧。元高文秀有《黑旋风敷演刘耍和》杂剧,今不传。[煞]是套数里煞尾的曲调,但为了充分表达曲意,可以增加调数。调数大都倒数,象这里的从[六煞]到[一煞]。这里[煞]曲是般涉调用的,句格与正宫、南吕、双调等的[煞]曲不同。“赶散易得”二句,夸说自己的演出非赶散的班子可比。赶散,指赶场的散乐。妆合,即装呵,指勾栏里的演出。
[五]五煞全曲:这曲写庄家交了二百文的高价进了勾瘭时看到的情景。木坡,指观众坐的看台。钟楼模样,指戏台。人旋窝,指拥挤的观众。台儿,指前台中间靠后边的座位,是伴奏乐贡的女艺人坐的,当时叫作乐床。旧时民间习俗。每逄神诞日,群众敲锣打鼓迎神出庙,周游街巷,谓之迎神赛社。
[六]四煞全曲:写付末开场。当时院本演出以五人为一伙,出场时付末站在中间,央人货(即殃人货,犹言害人精)即指他。下面几句形容他的脸谱、服色。直裰,长袍。
[七]三煞全曲:写开场时一段小演唱,当时叫作艳段,也即是爨。《梦梁录》:“杂剧中末泥为长,每一场四人或五人,先做寻常熟事一段,名曰艳段,次做正杂剧,通名两段,”下面演的《调风月《刘耍和》》,就是在艳段演出后的两段正杂剧。临绝末,指临近艳段结束的时候,杂剧就要上演,所以说:“爨罢将么拨。”么,即么末,指杂剧。
[八]二煞全曲:续写《调风月》的演出。这场小戏共有三个脚色,付末扮小二哥,付净扮张太公,旦扮帘下妇人。铺谋,设计。
[九]一煞全曲:写《调风月》的演出。张太公处处受小二哥的调弄,最后把皮棒槌都打成两半。皮棒槌,也叫扌盍瓜,是付末打诨时用的,槌头用软皮包棉絮做成,打时不会痛。刬(chan)地,平白无故地。
[十]尾声:写庄家汉因急于入厕半途出场,看不到后面精彩的演出,引起旁人的发笑,驴颓,驴的雄性生殖器,骂人的话。
[作者简介]
杜仁杰(约1201—1282年),原名之元,又名征,字仲梁,号善夫(“夫”也作“甫”),又号止轩。济南长清 (今属山东济南市)人。元代散曲家。《录鬼簿》把他列入“前辈已死名公。”他由金入元,金朝正大中与麻革、张澄隐居内乡山中。元初,屡被征召不出。性善谑,才学宏博。平生与元好问相契,有诗文相酬。元好问曾两次向耶律楚材推荐,但他都“表谢不起,”没有出仕。其子杜元素,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,由于子贵,他死后得赠翰林承旨、资善大夫,谥号文穆。
杜仁杰出生于诗书之家。父杜忱志行廉洁,有文名,进士及第授京兆录事判官,后因病归里。仁杰淡于名利,一生未仕。一生淡泊于功名,不求仕进,却把大部分岁月流连于山水之间。金末,他隐居于河
南内乡山中,与友人麻革、张澄等以诗相唱和;入元,屡征不就,隐居长清故里,居住在灵岩寺内的石龟泉畔,优游于灵岩、五莲山之中,并谒曲阜孔庙,登泰山,留有多处碑文、游记和墨迹。
在残曲[双调]“蝶恋花”中,他说自己“难合时务”,把“荣华”、“品秩”看作“风中秉烛”、“花梢滴露”。他认为世人只看官禄,不辨贤愚;只认金玉,不识亲疏。对昏暗腐败的政治现实,他无力改变也不想去改变,只好洁身自好,保持住自己一点节操。因此,金正大中,他与麻革、张澄隐居内乡山中;入元,屡征不就,隐居于长清故里,伏游于灵岩和五峰山之间。其子杜元素,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,因赠翰林院承旨、资善大夫,卒谥“文穆”。葬长清东北王宿铺西里许,墓已不存。
杜仁杰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,祖、父对其文学传教熏陶,使他在诗、词、曲、文诸方面具有良好素养。金正大元年(1224),杜仁杰离家南游汴梁,参加金廷科考未中,乃滞留京师,结识著名诗人元好问。开兴元年(1232)元军与金军战于钧州三峰山,金军大败,是为“壬辰之变”。杜氏于乱军国北渡黄河,逃归长清,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信的游历生活。这时严实“称藩于东平,以长清为汤沐邑,往来其间,能折节下士”。请名流学者“延教其子”,“兴办长清庙学”,“一时名士会聚于此”(《长清县志》)。杜仁杰、张澄、商挺等即于此时成为严实的门客与政治谋士,家庭教师。严实卒后,其子忠济、忠范、忠嗣相继任东平行台。这段时间约从乃马真后称制到至元初的二十余年间,正是杜仁杰的中年时期,是在东平严氏幕府中度过的。此时的东平,聚集了一大批金亡以后的名流人物,如元好问、王磐、王鹗、商正叔、商挺、宋子贞、李治、李昶、刘肃等,为教化方、治理东增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在这中间,杜仁杰与严氏子关系尤为特殊,一方面都是长清人,有同乡之谊;另一方面,杜与严实有知遇之恩,与严氏史弟则亦师亦友,志同道合;还有,杜氏在东平行台和东平府学谋划出力颇多,却始终示出任正式职务,无心仕途,处于隐、仕之间,很让严氏放心。在杜仁杰的鼎力辅佐与策划下,严氏办了三件深得民心的事:第一,宣扬孔孟仁慈爱民的王道,反对元朝推行的野蛮劫掠的霸道。以德养民,以礼养士,深得东平民心。他建议严实改“善善堂”为“种德堂”,以教严氏子孙和辖内百姓修德行善。这在当时具要的现实意义。第二,兴学养士。中原战乱未定,严实率先办起东平府学,不仅吸引了大批名流学者,为东平繁荣发展起了重要作用,还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与文化人才。如前列举的人物,大都做了元廷的高官,后起之秀如王恽、王构、王旭、李谦、徐世隆、孟祺、阎复、高文秀、张时起等,亦成为朝廷官员和著名诗人、戏剧家。所谓“东平庙学(即府学)……教养诸生,后多显者”(《元史·严忠济传》)。第三,兴礼乐以化民,改变杀伐之音。金亡后,严实首先把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从汴京请到东平,行礼乐之教,并为元廷输送了一批礼乐人才。严氏父子治理东平的四十余年间,曾数次至曲阜祭孔,意在宣扬孔孟的仁义礼乐之教,把东平治理成为一方“王道乐士”。上述种种,杜仁杰居间筹划力行,功不可没。
至元初年,杜仁杰约六十五岁,是步入晚年的老者了。此时东平行台严氏兄弟相继去职家居,杜氏靠山失据;加之行政区划变动,东平散府,新任执政者与其关系不似严氏亲密;另外,长期在东平患难与共的老友或入京为官,或去各地任职。约在至元二年(1265)后,杜仁杰便离开东平,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,他隐迹山林,徜徉于泰山、灵岩、长清、济南之间。大约在至元十九年(1282)逝于长清老家。杜仁杰之了杜无素,字质,曾任福建闽海道廉访使,杜仁杰因此被赠为翰林承旨、资善大夫,谥文穆。杜氏著作有《逃空丝竹集》、《河洛遗稿》,惜皆早佚。现存诗作二十八首,词二首,散曲六首,尚不足九牛一毛。
(文章来源招生考试网,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: https://www.sczsxx.com/html/read/gushi/2014071234697.html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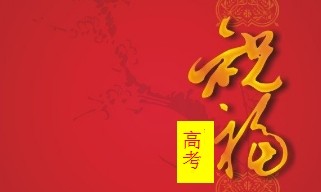
![2015四川高考分数线预测[文]:近6年分数线走势分析](/uploads/allimg/140626/1-140626102540H6-lp.jpg)

